有这样一位妇人,很不幸地身居恶邻之畔,邻居家是当地一门四进士的顶级簪缨世家;更不幸的是,恶邻屡次三番谋夺自家房产;最不幸的是,丈夫家祖上是恶邻的奴仆。
最终,他们抓住机会将丈夫堵在家门内,百般胁迫他签订让渡房产的契约,丈夫誓死不从。在备受侮辱之下,丈夫忍无可忍,自杀身亡。
当你是这位妇人,面对这样的情形,会如何处置?是哭哭啼啼安葬了丈夫,然后签下卖房契,孤儿寡母另找地方苟且生存,还是找这个跺跺脚整个地方抖三抖的超级缙绅豪族讨个说法?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初一,南直隶常熟人祝化雍的妻子王氏,就是面对这一惨况的妇人。祝化雍已经变成了冰凉的尸体,而她手上只有一纸丈夫临死前写下的遗书,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我死之后,儿孙们是要学伍尚引颈就戮,还是学伍员为父报仇,一切悉听尊便,为父都感激在心。”
伍尚、伍员出自中国历史中一段典故。春秋时,楚平王要杀大臣伍奢,就写信给伍奢两个儿子,对他们说,如果他们都回到京城,就赦免伍奢。
两个儿子明知道是陷阱,能怎么办呢?作为长子的伍尚对弟弟说:“如果回去能赦免父亲,那就该我去,这是孝道;而你赶紧跑到吴国去,如果我们父子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想办法为父报仇。”
然后,伍氏兄弟两人分道扬镳,伍尚回到京城随父亲同死,伍员投奔吴国,最后借兵灭楚,鞭尸楚平王,为父兄报仇。这一典故千百年来为人传唱。
祝化雍这几句遗言是人生最后的呐喊:儿子,你们要为父亲报仇啊!
王氏拿着这张字字泣血的遗书,心中悲愤无助。她清楚地知道自家仇人到底是怎样强大的存在。
常熟赵氏,一门之中进士、举人迭出,在朝野做官的大神数不胜数。直接逼死丈夫祝化雍的赵士锦,在崇祯十年(1637年)丁丑科中进士,时任工部主事。
赵家从赵士锦的曾祖父赵承谦一代发迹。赵承谦乃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司参议。
祖父赵用贤更是显赫,为隆庆五年(1571年)同进士出身,官至吏部侍郎。天启初年,追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明史》有传。只看“文毅”这个谥号就知道赵老太爷有多牛。明朝官员谥号中能用“文”字,得是科举前列、能够选入翰林院的超级做题家。“毅”字还在明朝谥法中名列前十,整个明朝能谥作“文毅”只有区区十三人而已,且都是解缙、三元及第的商辂、宰辅张四维这样的牛人。
赵士锦父亲一辈,有伯父赵琦美,以父萌补官太仆丞,官至刑部郎中;父亲赵隆美,也以父荫为官,官至叙州知府,在奢安之乱中能指挥若定,保一方平安。
到了赵士锦这一辈更是科运兴隆,长兄赵士春是全国顶级学霸,与弟弟同科登第,高中探花。
不仅如此,赵家的姻亲也很有实力,赵士锦的亲家陈必谦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
赵家还是东林党的骨干力量,赵士锦有个早亡的二伯祖美,因名噪一时,连东林党大佬杨涟都亲临病榻旁嘘寒问暖。
在大明苏州府,能持续百年科运的家族非常罕见,归有光说过:“吾吴中,无百年之家久矣。”通常都是显赫个两三代,便逐渐衰落,但从赵承谦嘉靖年间及第到赵士春、赵士锦兄弟双双报捷,赵家之盛正好一百年。
由此可见,赵家四世高门,百年簪缨,姻亲势力盘根错节,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是当地各级官员都惹不起、躲着走的庞然大物。
反观祝家,苦主祝化雍虽有功名,也不过区区举人而已,官职只是一县教谕。让举人的遗孀去与这样的豪族巨擘为敌,这不是螳臂当车、飞蛾扑火吗?
但王氏却偏偏不信邪,非要给亡夫讨个公道。她坚信,就算是飞蛾扑火,也能闪出一瞬的光辉。
从奴到官,鲤鱼可以跃龙门吗
常熟县是大明南直隶苏州府属县,作为江南膏腴之地,常熟既是经济发达之地,也是文风鼎盛之乡。自唐至清,区区一县出过进士四百八十八名,其中状元八名,榜眼四名,探花五名。
在这个小县中,科举就如今时今日考公一样,是所有人的信仰,对祝化雍来说同样如此。经过十年寒窗苦读,祝化雍终于在天启元年(1621年)高中举人,当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即使在常熟,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为什么这么说呢?常熟属于苏州府,苏州、常州、松江三府所在的南直隶,是整个大明最难考取举人的地方。在晚明,南直隶的每次乡试都有超过六千名秀才参加,而中举名额只有一百三十八个,通过率仅2.3%;相比起来,举人考进士就“容易”多了,全国加起来就四五千人,冲击三百个名额,通过率至少有6%呢。所以,祝化雍能考中南直隶举人,在当地可算是一鸣惊人,要知道那一届乡试常熟中式者不过三人。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形:当省里派人来到常熟祝家,向祝化雍报捷中举的时候,祝家肯定门庭若市,乡里同贺,这可是光宗耀祖的辉煌时刻。“范进中举”的盛况在祝化雍这同样上演了一遍,不到三十岁的祝化雍也到达了人生的顶峰。
其后祝化雍屡次进京赶考会试,但终归功亏一篑,没有再向前一步。但这也没关系,举人在明朝已经是鲤鱼跃龙门了,考中举人,就正式踏入“官”的行列,虽然一开始授官不大,通常会从一县的教谕、主簿、典史之类的开始,但无论如何,他已经算跨过了官民鸿沟。
从此以后,祝化雍家门口会有一块木牌,上书“辛酉科举人”字样,这便是代表此户主人社会地位的举人牌,当官吏收税的时候,这一户人家必须跳过。
同时这一家的主人在没有外出做官的时候,是维持地方秩序的乡绅。他可以给知县写信,下款称“治愚弟化雍”,即举人与知县可以称兄道弟。诸生见知县叫作“禀见”,举人见知县则属拜客,是平等往来。举人见了知县平起平坐,举人要是不主动告辞,知县不敢主动提出送客,如果坐到饭点,知县请吃饭也是必需的。而且由于这家主人有权随便见知县,于是就出现了“请谒有司居间”的现象,即通过自己的身份居间为乡里乔事、说情。
州、县缙绅普遍参与地方政事,没有他们的支持,州、县官员大多不敢以一己之意擅自行事。遇到县中应办却难办的事情,如公益事业,举人可以出面同地方官说一声,几乎没有办不成的。
若有良民受土豪劣绅的欺凌,申诉无门,只要举人们去找知县讲明真情,也可获得公正处置。这样的举人,只要他平时注意一下公众形象,便会在地方上形成明星效应,哪怕是泼天大事,只要他出面讲几句话,就可息事宁人,因为乡人无不敬仰他,对他言听计从。
以上是政治身份,有了政治上的地位,经济上也不会差。举人家中田亩有免税额度,不用服徭役,特别是后者,这在大明是可以破家的苦差。一成为举人,周遭商人、小地主都愿以家产投寄门下免除税差,举人自然能分得他们一部分收益;而破落户小民则愿意通过卖身成为举人家的奴仆丫鬟,换取不用服徭役的好处,且能混得温饱。
所以一旦中举,就可保证衣食无忧,从来只有饿死的秀才,没有缺钱的举人。“范进中举”里表现得非常形象: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中举后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更不消说。
祝化雍在天启元年的这一场大造化,某种程度上算是改变人生的一役。从此他也可以跻身上流了,比如地方有公事(修桥铺路、赈济灾荒之类的事)的时候,就会召集地方缙绅开会,祝化雍便有了出席的资格。
有一年冬天,祝化雍参与了一次地方缙绅会议。入场时,他碰到了当地另一位孝廉沈公,这位沈公看到化雍,就嬉笑着对他说:“你看,今天真是冷啊,我这鼻涕又忍不住流了出来。”这句看似和气的寒暄,却引起了在座士绅掩面哂笑。
全场之下,唯有祝化雍一脸难堪,只能赔着笑脸与在座诸公打着哈哈。为什么一句“流鼻涕”,会让祝化雍陷入如此尴尬的情形?同为孝廉,为何沈公要出言讥讽?祝化雍身上又有怎样的难言之隐?
翻开明崇祯年间《常熟县志·选举志》,我们能看到当地在天启元年(1621年)辛酉科总共有三人中举,分别是钱赓、顾懋勋、顾化熙。刚才不是说,祝化雍在这一年中举吗,为何县志中没有他的名字?
在《选举志》中,顾化熙名下还有一行小字——“字来仲,姓祝,授丹阳县教谕”。看到这我们多少有点醒悟:这位顾化熙是否与祝化雍有点关系?没错,两个名字都属于那位原名为祝化雍的兄台。那为何他在乡试的时候要改名换姓去考呢?
这是因为,祝家祖上实在混得不怎么样,曾投入常熟海虞陈家为奴。对祝化雍而言,祖上为奴,则世世为奴,只要一天不脱离与主家的干系,便是奴仆身份。吴地俗语以奴仆为鼻,涕从鼻出,就是揶揄祝化雍的奴仆出身,士绅们显然因祝家先祖之故不屑与祝化雍为伍。
奴仆就如打在祝化雍身上的烙印一般,即使他已经鲤跃龙门了,士绅们仍然以此耻笑于他。那么,为何奴仆身份会是祝化雍无法摆脱的黑历史?
在明朝,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奴隶,而是相当于家丁(家中仆役)、农奴(无人身自由的佃户),他们通过罪罚、买卖、投寄、继承等方式成为奴仆。典型的例子是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唐伯虎卖身葬父进华府,便成了华府的家丁仆役。他不是自由人,属于华府的财产。奴仆人身属于主人,主人分家时,可以将奴仆与其他财产一起分配,也可以将他们出卖和转让。
在祝化雍所处的吴中地方,蓄奴风气非常兴盛,一个官宦人家有一两千奴仆并不奇怪。前面说过,有的人为了躲避赋役,会将人身财产投寄到缙绅门下,也有人活不下去了卖身为奴。
男子入富家为奴,会立下人身契约,终身不得自由,主家有事,必须呼之即来,且子子孙孙不得脱籍。即使有的奴仆家里有钱,花钱赎身,名义上脱离了奴仆行列,但实际上也无法与主人家并肩而立。
祝化雍的先人就在类似的情况下,进了常熟官宦陈必谦家为奴。陈必谦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癸丑科同进士出身,排名虽不高,但官做得不错,崇祯年间曾任河南巡抚、工部尚书。陈家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官宦门第。
但祝化雍并不甘心世代为奴,心中燃起了通过科举提升自身地位的念想。只是这不是仅通过刻苦攻读就可以实现的,奴是贱籍,在当时与勾栏、乐户、疍家、乞丐等都是低人一等的身份。
在对贱籍的歧视中有一点很要命:《大明会典》规定奴仆、娼、优、隶、卒等贱籍不许参加科举。对一心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祝化雍而言,这不啻一条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让他永远无法挣脱命运。
时间久了,为贱籍有志之士鸣不平的大有人在,认为国家凭文章取士,在奴仆中有贤才的,怎么就不能参加科举呢?不过呼吁归呼吁,终明一朝都没有放开对贱籍的限制。
但限制事小,“考公”事大,对在任何时代都有“考公”信仰的中国人而言,办法总比困难多。既然有需求,就一定有解决办法,在大明出现了“冒考”这种操作,为贱籍解决了考试资格的问题。
所谓“冒考”,就是贱籍顶替良民身份获得科举资格,比如可以冒名顶替某位不会参加科举的人,或者以过继的形式投靠到他人家中,金蝉脱壳。在打通关节后,家里再上下使钱,找到五个一同参加考试的童生联名互保,反正那时候没有身份证,没有照片,加上明朝府县考官对此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贱籍者可以搞定乡里乡亲,无人举告,那就民不举官不究了。因此不少贱籍民众通过“冒考”改变了人生。
从祝化雍改姓为顾这个细节,基本可以了解他的手段大概率是过继到顾家,然后以此洗脱贱籍,获得科考资格。虽然史书上没有明说,但可以合理推断祝家虽然祖上是奴仆,经过几代的努力,至少到祝化雍这一代家里已经略有家财,可以供养子弟读书,也可以打点上下。
只是,即使通过“冒考”考中举人,祝化雍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同乡同里谁都知道他原名是祝化雍,家里曾是奴仆。父老乡亲也都瞧不起他,如果“不幸”与他碰面,充其量叫一声“祝举人”,有的人则干脆视而不见,招呼都不跟他打一个。
本来这也没什么,祝化雍坚信自己是家族改天换命的开端,只要忍人之所不能忍,未来,家族持续在科场斩取功名,持之以恒之下,总有一天祝家能获得乡里的真正尊重。
但祝化雍没有想到的是,一场祸事正在自家隔壁酝酿,且终有一日将他逼入死地。
对一座祖宅的强取豪夺
祝化雍一家住在常熟城南的祖宅里,据说这座宅子风水好,祝家居此之后逐渐发家并出了个举人便是明证。祝化雍打算一边读书准备再度进京赶考,一边等着授官出仕,小日子过得也蛮滋润。
崇祯九年(1636年)秋天,祝化雍突然听到了非常熟悉的喧天鼓乐。一支来自南京的报喜队伍敲开了隔壁家的大门,原来是他的邻居赵士锦在丙子科南直隶乡试中突围而出,高中孝廉。
本来这是好事,邻里两家先后中举,在士大夫圈子里也是美谈啊。但这只是普通人的看法,对于赵家可能并非如此。
赵家此时还是常熟的顶级门宦,但在崇祯年之前,赵家的情形还是有点古怪。自从赵承谦、赵用贤父子先后考中进士后,赵家已经多年未在科举上有作为了,赵士锦父亲那一辈,琦美、祖美、隆美哥仨,一个中举的都没有。
赵家再有人中举已经是天启七年(1627年),赵士锦哥哥赵士春在这一年考中举人。赵家从赵用贤隆庆五年(1571年)中进士到赵士春中举,在科举上断层了五十多年。
另外,赵家大神赵用贤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就死了,人走茶凉,直到天启三年(1623年)赵用贤才获得恤典,加荫家中三个子孙做官,也就是说,赵家有将近三十年时间家中是无人做官的。且琦美、隆美即使依靠父荫当了官,相比于科举正途,荫庇出身的人在官场是低人一等的,顶了天也就做到知府。
祝化雍一个奴仆出身的贱籍,竟然能在天启元年(1621年)考中举人,这会给当时正处于家族低谷时期的赵家带来怎样的感受?史书中没有提及,但人们可以合理推测,肯定不是滋味。
幸亏赵士春、赵士锦兄弟争气,在天启、崇祯年先后中举,一洗笼罩在这个家族头上半个世纪的郁闷。赵家到了这时可以用“中兴”来形容。
而且在赵士锦中举一年后,崇祯十年(1637年)赵氏兄弟俩和祝化雍一同赶赴京城参加会试,结果是赵士春考了个全国第三,高中探花,赐进士及第,赵士锦也冲上全国第二十二,以二甲第十九名赐进士出身,而祝化雍却再度落榜。
对赵家而言,这是重回巅峰的一战,不仅打破了归有光关于吴中大家旺不过百年的魔咒,还让赵士锦扬眉吐气,在面对邻居祝化雍的时候,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种“你爹还是你爹”的畅快?
常熟民间风评,此番中兴让赵家气焰熏天,而以士锦为最,乡党给他六字评语——“尤贪悍,肆凶虐”。因为他在家里行四,乡党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四大王”。风评如此之差,是不是真实的呢?可能性不小,因为在崇祯《常熟县志》里他哥哥赵士春和他堂哥赵士履都有传,但偏偏作为全国第二十二名的他没有。
赵士锦一朝进士第,便把威来行。他秉性贪婪无理,盯上了一墙之隔的邻居祝化雍。赵士锦琢磨着如何将祝家房产给霸占了,使自家进士府邸得以扩大。
地方豪门大户逼买侵占邻居家产的事件,在江南之地时有发生,有的还造成不小的骚乱。如万历十五年(1587年)九月,苏州的原兵部尚书凌云翼儿子凌玄应,依仗老爹的权势横行霸道。他也看上了邻居章士伟家的房子,想方设法要把章家宅子占了去。
凌家百般威逼利诱,章士伟胳膊扭不过大腿,答应成交,但正好赶上章老太太病故,章家遭遇丧事,多了支出,因此想让凌家多给一点钱,才愿搬家。凌家自然不肯,就派出奴仆驱赶章士伟,双方一来二去发生了争执,结果凌家奴仆一不小心将章士伟殴打致死。
闹出人命之后,作为章士伟同学的乡里生员去找凌家理论,结果凌玄应又以武力解决问题,派出奴仆打手数十人,关起大门,将理论的生员三人狠揍一顿。生员伤的伤,残的残,其中一名生员张元辅不堪受辱上吊自杀。事情闹大之后,凌玄应跑到南京上下打点,花了很多钱才勉强把事情平息下去,而凌玄应本人只受到小小惩处而已。
看来一旦家中得势,占有邻居房产以扩大门庭,已成了江南的陋俗。这一次的当事人是赵士锦,他想出了比凌玄应更狠的招数,就是抓住祝家的奴仆身份做文章,竟然要求祝家归还所占主人家房产。
赵士锦认为:首先,祝化雍先人投入陈家为奴,历经几代,直到现在,关系仍然存在;其次,赵士锦与陈必谦成为儿女亲家,陈必谦的女儿嫁给赵士锦的儿子,祝家所住的祖产已经由陈必谦作为女儿的嫁妆赠送给赵家。综上理由,赵士锦让祝化雍签字画押,将房子让与自己。
亏得赵士锦能想出这样的三段论,他的逻辑在今天看来就是强盗逻辑,但在当年却还真有几分道理。想要了解赵士锦的法理基础,就得再度回到奴仆与主家的关系中。
前面讲过,奴仆大体分成家仆和佃仆两种,前者主要卖身,后者不仅卖身,还要租佃主家土地。也就是说,无论哪种,奴仆的身家财产全部权利归属于主人家,奴仆也有世世代代为奴的“世仆化”倾向。
在明朝的司法实践中,构成佃仆身份的要素是“佃主田、住主屋、葬主山”;当主家的地产、房屋转卖或转赠他人后,奴仆转属新主人;主仆关系可以解除,前提是仆人离开主人的土地、房产、坟地等。
在徽州诉讼文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祁门县许文多的祖父在正德年间将一半家产卖给别人,后来传到了郑相达手中,许文多又从郑家手中租佃了原属自家家产的田地。隆庆年间,许文多又将自家居住的房屋田产卖给郑相达,然后租借了房屋。于是许文多成了郑相达的庄仆。但许文多因田地、房产都是原来自家的产业,非常不甘心作为奴仆被郑家使唤,于是在万历年间到县里进行诉讼,希望脱离主仆关系。官府判定,想解除佃仆身份也可以,但必须退还租佃郑氏的田地,搬离郑氏的房屋。许文多无奈,只能留下继续为仆。
事情还没完,天启年间,许文多的侄子许尚富积累了一定的财产,就另建家宅,企图脱离主仆关系,被主家再度告上县里。县官仍然维持之前的判决:许尚富只有脱离郑氏土地,退田退房,才能解除佃仆身份。
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在明朝的乡规律法之中,奴仆想脱离主家,或者洗脱奴仆身份,必须具备同时脱离土地和房产的条件。
像许家卖掉房产田地给徐家,又重新租回自家田地,官府仍然认为许家人就是奴仆,想离开主家就得脱离主家产业。与许家卖产类似的还有诡寄,即一些有田产、房产的人为了逃避徭役,会将自己的财产一起投寄到乡绅官宦的门下,那这些财产也会被视为主家的财产,纵然人可能仍然住于斯耕种于斯,但收获的一部分也要给主家占去。
那么问题来了,赵士锦提出交涉的房产,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不是祝化雍家早已卖出,或带产投寄的产业呢?我们先看看交涉发生后两方的态度。
在赵士锦提出交涉之后,祝化雍既没有寻求同乡缙绅出面说和,也没有诉诸法律,找县、府官员讨回公道,而是采取了“三不”政策——不见面、不理睬、不冲突。
乡人评价祝化雍,说他是狷介之士,以今天的话翻译就是“耿直boy”,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老实巴交。作为一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祝化雍不善于与人争执,只是一直躲着赵家,坚决不与对方见面。
赵士锦看对方的“乌龟策略”,也是不依不饶,几番追问,只找到祝妻王氏理论。王氏也装傻,一推四五六:“我家官人不在,奴家不敢做主。”
有见及此,赵士锦火大了,但对方毕竟是举人,不能像凌玄应那般直接派出仆人去强行拆迁。于是,他就命家中奴婢天天隔着墙咒骂祝家,什么难听的话都递过去,令祝家人无法抬头。
祝化雍为此忍受多年,实在没办法,就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在天启年间谋得了一个丹阳县教谕的芝麻绿豆小官,因此长期在外,极少回家,以这样的方式躲避对方的纠缠。
虽然赵士锦这个嫁妆赠予的借口看上去挺扯的,但为什么祝化雍既不同意也不拒绝,而是采取了拖延、回避的策略,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又有一些心虚理亏的感觉。
史书里没有说明祝化雍所住房子的产权渊源,那么祝家房产有三种可能:第一,是祝家人成为奴仆后,主人陈氏租给或借给祝家居住的;第二,是祝家为奴之后发家致富,自己花钱置办下的;第三,是祝家在成为奴仆之前就置办下的,在投身为奴时一并带入了陈家。
从争议大小来说,第一、第二两种的争议都不大。如果是陈氏的房子,陈氏有充分理由收回房产;如果是祝家后来买的房产,那也在法理上与主人家关系不大。
既然赵士锦敢这么催逼,那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祝家带产投寄,也只有这种情况,祝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理亏,既不舍得脱离名义上属于陈氏,但实际上属于自家的房产。
但无论哪种,两方都没有出示过硬的证据,赵士锦无法提供陈家嫁妆附带的文契,祝家也没有可以证明房产是自家合法拥有的契约,便造成了两方僵持不下的局面。
事情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冬终于有了解决的契机。这一年又逢京城会试,各地举人再度齐聚京师,争取进士功名。二十多年来每战必与的祝化雍,自然也要赴京赶考,万一考中了呢?是不是就能逆转在房产纠纷中的不利局面?
结果,没有意外地,祝化雍与以前一样还是名落孙山。只是,这次祝化雍有点大意了,从京城回来后,他没有回到丹阳任上,而是直接回了家。此时正在家中守孝三年的赵士锦正好把祝化雍堵在了家里——终于等到你了,咱们解决一下问题吧。
祝化雍自尽,留下复仇遗书
为了得到祝家房产,赵士锦也并非完全是空手套白狼,而是愿意出钱购买。在堵住祝化雍后,赵士锦让人逼迫祝化雍收钱立契,以图结束这场持续了几年的拉锯战。
只是耿直老实的祝化雍就如那头死不低头喝水的犟牛,任人把嘴皮子磨破了,就是不肯签字画押,还是紧闭家门坚决要做缩头乌龟。
赵士锦见祝化雍油盐不进,终于忍不住了,盛怒之下,再度命手下奴婢开骂,又命家仆砸墙拆迁,将两家之间的院墙凿出个大洞,实现了两家合一的“夙愿”。
祝化雍夫人王氏跑到赵府理论。对于女流之辈,赵士锦也命自家老婆儿媳出来应付,两边女眷扭打在一处。赵家这边人多势众,王氏头发被抓掉一把,身上衣裙被撕裂,举人妻子遭受了莫大的侮辱。
多年来的屈辱、骂名,还有凿墙拆迁的重锤,如万针穿心,使得为了家族振兴、摆脱贱籍而数十年奋斗不止的祝化雍终于精神崩溃。他拿过纸笔,写下了人生中最后几句话,然后将三尺白绫挂到房梁之上——未及半百的他结束了自己屈辱的一生。
后来祝家在诉冤揭帖上的说法是祝化雍被赵府囚禁,用绳索绑住拷问,祝化雍是死在对方手上的,赵家还对尸体进行了搜查侮辱。但祝化雍留下遗书明确说是上吊自杀,与诉冤揭帖并不符合,如果尸体被搜查,遗书又如何能落到祝家手中呢?所以祝化雍上吊于家中才是事实。
家里人发现时,祝化雍已经命丧黄泉,只留下一张白纸和几行遗书:
行年未五十,被恶邻赵士锦逼占祖基,朝夕詈骂,辱及尔母,凌虐万状,含冤自经。虽类匹夫小谅,实出万不得已。横死之后,为伍尚者,为伍员者,听儿辈为之,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父含泪遗嘱。
其中“匹夫小谅”出自《论语·宪问》:“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管仲是齐桓公的相国,相传他发达前曾为贱业,孔圣人意思是,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也不过守着“匹夫匹妇之为谅”,“小谅”就是“小节”的意思,指小人物恪守的体面和节操。祝化雍在四个字里就一语双关,既以出身微贱的管仲自比,又表明自杀是为了明志,保持不为强暴屈服的节操。
“为伍尚者,为伍员者,听儿辈为之”,典出《春秋左氏传》,前文已经解释过了。伍尚为救父献身是孝,伍员报仇是仁,祝化雍是在让儿子自己掂量应该怎么做。
这短短几行遗书,倒是非常能体现祝化雍的学术功底和节操,只是最后这句话奠定了祝家未来行事的基础。
不过,该怎么行事,该如何报仇?对祝家而言,报仇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时,摆在孤儿寡母面前的路并不多,最简单的是息事宁人,忍辱负重,签字画押,避免与强大的对方发生正面冲突。但任谁拿着这份血泪遗书,都不太能咽得下这口气,除非王氏是那种没什么见识、懦弱无知的妇人。
但从祝家前前后后都由王氏出面应付,且还敢和赵家人理论厮打,就能看出这位妇人绝非等闲之辈,她纵然不是家中主心骨,至少也是敢于抛头露面、据理力争的明白人。
王氏首先想到的是请当地缙绅,也就是未出仕但有功名,或者居乡的前官员主持公道;另一边的赵家遇到对方刚烈自尽,也需要找缙绅说和。双方都有需要,那么找谁合适呢?

钱谦益
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常熟乡里,还真有一位大神坐镇,他便是鼎鼎大名的钱谦益。他与柳如是红袖添香的故事,由陈寅恪大师考证,已经路人皆知。此时这位大明的探花、儒林的泰斗、清流的领袖——钱谦益年过花甲,刚迎娶柳如是不久,正是新婚燕尔、夫妻情笃之时。
这一年,钱谦益卖掉珍藏的宋善本《汉书》,在半野堂之后新筑了绛云楼两层五楹,作为和柳如是的新居,并广纳藏书数万卷。
春风得意的钱谦益毫无疑问是此时乡邑中最有分量的名人。大明缙绅居乡时,有权武断乡曲,乡间一些普通民事诉讼,有名望的缙绅便可平事,不需要闹到官府。
但是面对这个棘手的案子,钱谦益选择了回避。他闭门谢客,表示这事他管不了。作为清流领袖,平时道德文章写得花团锦簇的钱谦益,为何面对此事当了缩头乌龟呢?
那是因为钱谦益没法表态。士大夫家族互相联姻,关系盘根错节,比如赵士锦与陈必谦是儿女亲家,钱谦益与陈必谦也有亲戚关系,陈必谦的母亲是钱家人,钱谦益还亲笔为陈母写过诰命。
如果偏向祝家,那岂不是一下子得罪了两个簪缨大家?如果偏向赵家,乡亲们会不会骂他庇护豪虐?在钱谦益看来,此事无论如何都会让他里外不是人。但不表态,也相当于表态——钱谦益是偏向于祝家的。
请缙绅主持公平行不通,王氏毫不犹豫地做了第二个选择——告官。自己丈夫是举人出身、朝廷官员,总不能就这样白白死了。祝家人把祝化雍尸体抬上县衙大堂,击鼓鸣冤。
但很快他们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对头作为常熟顶级簪缨家族的威力此时就显现出来了。县衙的处理迟缓冷淡,尸体放在公堂七日了,地方官也不敢上报,更没有派衙役将赵家的人提来问话,而且邻里慑于赵家气焰不敢出庭作证。
这分明就是地方官,因为案情关系到当朝两进士的赵家而畏首畏尾。而且这种因争夺产业引起的纠纷,历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不过眼下苦主一家死了人,且死了一位举人,地方官更要小心翼翼处理。
此外,官府冷处理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此时的常熟县衙正好处在权力真空之中。上一任知县刘定勋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十一月上任,为官仅仅一年就死于任上。王氏诉诸县衙时朝廷正在选拔官员前来续任,而新任知县曹元芳要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才到任。
但王氏只会觉得是赵家只手遮天,难道即使祝化雍死了,仍无处讨个公道吗?
还别说,前面说过的苏州凌尚书家逼买民宅案中,纵然苦主被打死,主持公道的生员被羞辱自杀,凌家也不过是受到轻微的惩处,人近乎白死了。相信整个常熟的人都不会忘记当年的事,现在他们都在看,这样一起逼死举人的纠纷到底会以怎样的结果收场。
此时,事情已经明显朝着不利于王氏的方向发展,无论是诉诸乡绅还是官府都没有得到说法。他们一家孤儿寡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官人尸体都过了头七了,也差不多要下葬了,只是人一下葬还能去哪里诉冤呢?
倔强的王氏只能使出最后一招——官府路线走不通,那就走民众路线。
王氏复仇记
祝化雍出仕后一直在丹阳做教谕。明朝县有县学,负责县内文庙祭祀,以及管理、教育一县的秀才,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局长。祝化雍因为是老实、耿直的人,在工作时能够贴近群众,平时对县里生员的学习与生活都非常上心,因此在丹阳生员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王氏想到了一条路子,就是找祝化雍的学生帮忙“公举”。所谓“公举”,就是乡贤就地方事务发表看法,他们通过与地方官沟通(面见或公呈)表达意见。有资格公举的主要是在乡官员,但秀才、德高望重的老人后来也有了这样的权利。
到了晚明,秀才们将公举演变成操纵舆论风向的手段,借着为民请命的名头,向官府表达读书人的态度,逼迫官府公正处理案件,由几名、几十名乃至成百上千名生员共同参与。一旦公举,地方官府必须给予重视,因为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大事。
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苏州昆山乡宦周玄暐撰《泾林续记》,这书多由嘉靖、万历年间典故所成,但里面许多记录得罪了不少当时的士绅与大家族,再加上周玄暐的儿子有仗势欺人的劣迹,于是乡里士民五百余人群起合诉,应天巡抚王应麟和督学、盐政二臣合疏上闻,周玄暐因而被逮。由此可见,乡间公举的威力有多大。
秀才们还利用地方官礼贤下士的风格,出入县衙,包揽诉讼,代表民众与官吏乔事。本来明朝并没有正式的讼师,过去讼师也大多是充军罪犯、闲散吏员和被革生员,但到了明中后期,生员也常有不顾体面的人,帮百姓写状子、递状子,入衙门打点勾兑。
对这些事王氏自然清楚,因此在百般无奈之下,她只能选择这一条路。于是王氏写了一封揭帖,也就是那时的大字报,把它贴到大街小巷,或者经人手传阅,用以带动地方舆论。
王氏一不做二不休,一下子印刷了五百余份,这个数字也显然是有的放矢——丹阳生员有四百多人,她就是要做到人手一份还有富余。印好揭帖之后,她把揭帖发往丹阳,动员祝化雍的学生们为老师讨个公道。
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丹阳诸生手里突然接到了这样一份揭帖,上面写下了自己老师屈辱的遭遇,文末写道:“愿诸君敦侯芭之谊,举鲍宣之幡,助我未亡人,执兵随后,共报斯仇,则大义允堪千古。”
短短一句里,同样是引经据典,大义凛然。“侯芭之谊”典故出自汉朝,讲的是汉代文化“大V”扬雄家穷又好酒,因为罢官回家,门庭稀落。不过总有些人投其所好,拿美酒佳肴跟随他左右一同游学,巨鹿人侯芭就是其中之一,他得扬雄传授深奥的《太玄》和《法言》,事扬雄为师。
扬雄的朋友刘歆觉得这些人都是叶公好龙,并非真心向学,跟扬雄说:“现在的人都是无利不起早,连《易经》都学不会,更何况《太玄》?我就怕他拿了你的书去盖酱缸。”扬雄听后笑而不语。日后扬雄去世,人走茶凉,更加无人问津,唯有侯芭为老师修筑坟墓,并且为老师守丧三年。
在此,揭帖作者将祝化雍比作穷困的扬雄,希望祝化雍的学生们以侯芭之谊为已经去世多日却仍未下葬的老师殓葬起坟,呼唤学生们勿忘老师的冤屈。
“鲍宣之幡”也是汉朝典故,说的是鲍宣为人刚正,敢对丞相执法,丞相孔光与御史中丞找了鲍宣的麻烦,把鲍宣以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之罪下廷尉狱。鲍宣的学生济南人王咸在太学门口打出一面大旗:“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太学诸生上千人集聚一堂,公车上书,终于为鲍宣解除死罪。
这个典故也是用得恰如其分,就是呼吁学生们如王咸救师集合起来,为祝化雍讨个说法。
假如你是丹阳学子,看着手中揭帖,想起侯芭对老师的不离不弃,想起王咸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义无反顾,岂能不热血上头,岂能袖手旁观?
这份揭帖虽以王氏名义发出,但四骈六韵,引经据典,典故渲染得恰到好处,令人热血沸腾,肯定是出于书生健笔。江南文脉昌盛,的确有些文化世家、簪缨大族的女性可以受到一定的教育,但对于一个奴仆家门,能否娶到高门大户受过教育的小姐,很值得怀疑。
所以,很大程度上,王氏应该是得到了当地某些读书人的支持,说不定还有与赵家不对付的当地其他科举家族的支持。总之,这份揭帖传遍了丹阳的大街小巷。
于是丹阳学子互相串联,几百位年轻人打起铺盖卷,自备粮食,浩浩荡荡穿州过镇,从丹阳奔向常熟。学子们抵达后,在老师家门口集会,振臂高呼,要为老师祝化雍申冤。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常熟的缙绅们再也当不得缩头乌龟了。当时赋闲在家的另一位晚明名臣瞿式耜出面,召集乡内缙绅们开了紧急会议,平息众怒。
瞿家也是常熟官宦世家之一。瞿式耜,字起田,是明末鼎鼎大名的人物,早年拜钱谦益为师,后中进士,为东林党后起之秀。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瞿式耜被弘光政权任命为广西巡抚,后来还曾拥立永历帝,最后为国殉节。
这位以身殉国的忠臣此时正罢官在家。他与赵、陈两家同为故交,之前也采取了回避态度,只是眼前面对孝义诸生,终于坐不住了。他出面召集缙绅,大家自然都要给面子出席。
丹阳学子也参加会议,对缙绅们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赵家逼死朝廷官员,惨不忍睹,你们常熟号称礼义之乡,理应问罪作恶之人,但为什么又首鼠两端,不管不问?我们虽然不过一介儒生,但也知道在三之节,如果你们不管,我们就去京师,击登闻鼓,告御状,为常熟的士绅一雪前耻。”
丹阳学子这番申诉的中心词是“在三之节”,这也是《国语》中的微言大义。晋国大夫栾共子说:“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大意是:父亲给我生命,师长给我教诲,国君给我食禄,所以人要始终如一地侍奉他们。
接下来栾共子还说了一句:“唯其所在,则致死焉。”只要是君亲师的事,就算拼了一条性命也要干到底。后来,栾共子果然奋战到底,为主公晋哀公战死。
丹阳学子这是以“天地君亲师”的大义,告诉常熟缙绅:在座诸公听好了,如果今天诸公不给一个说法,那么我们就算是为老师拼上一条性命,也要诸公给一个说法。
头举春秋大义,丹阳学子可谓有理有据,痛快淋漓,将与会的常熟缙绅们骂得抬不起头来。特别是要拼命的气概,让在座儒学大佬们心惊肉跳,不敢说话。
其实他们不说话,还是因为事关赵士锦和陈必谦,众人始终拿不定主意。他们还是要看大佬钱谦益的脸色。乡绅们安抚着丹阳学子:“我们说了不算,还是请钱谦益来公断吧。”
等了好大一会,钱谦益才姗姗来迟,瞿式耜将老师迎到堂中,将祝赵之间的矛盾和学子们的诉求前前后后讲个明白:“这事大家都没主意,只能请老师周旋。”
钱谦益果然是老狐狸,先问:“陈必谦老爷子意下如何?”因为祝化雍是陈必谦的奴仆,所以陈老爷子的意见也很重要。
瞿式耜说:“陈老爷子的意思是,冤家宜解不宜结,愿意讲和。”
钱谦益沉思了片刻,看看堂下义愤填膺的诸生,说了一句杀人不见血的话:“在陈既可以无君,祝亦可以无主。”然后起身拂袖而去。此言一出,丹阳学子顿时欢呼雀跃。
虽然钱谦益老谋深算,惜墨如金,但在此危急关头,也只好对不起陈家了。为什么说陈必谦无君呢?陈必谦年纪比赵士锦大,赵士锦也称他为兄,这事由陈家奴仆而起,一来闹出了人命,二来导致丹阳学子兴师问罪,已经酿成了地方骚动,快要造成民变了,但陈必谦作为维护一方稳定的士绅,不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岂不是辜负了君上赋予他们平时武断乡曲,维持地方秩序的权力吗?
这就是钱谦益所指的“无君”,特别是在常熟县衙无官的情况下,维持乡里稳定就是在座缙绅的事,所以钱谦益觉得陈必谦缺乏大局观,不能制止亲家赵士锦的贪婪逼占,酿成大祸。到了此时,钱谦益只能将陈必谦抛出来灭火。
“祝亦可以无主”一句则解除了陈祝之间的主仆关系,双方不是主仆,那赵士锦也就失去了逼占房产的主要理论依据。钱谦益一语定谳,为这件事下了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明显倾向于祝家的。
本来钱谦益想息事宁人,让陈必谦出面解决问题,但可能他也没想到,他的话让丹阳学子们觉得自己的行为已经获得了常熟大佬的支持,于是大伙浩浩荡荡前往赵家。而平时被赵家“四大王”欺压过的常熟士民也一同汇集到队伍中,很快聚集起上千人。
一行人来到赵家时,显然缙绅会议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赵家,赵士锦命家仆放锁闭门。但这对于群情激昂的学子完全没用,有几个人翻墙而入,打开门闩,人群一拥而入。
接下来的事便无人可制止了。丹阳学子和常熟士民将赵家抢拆一空,宅子顷刻被夷为平地。学子们在赵家地基上造坟埋葬了老师,完成了在三之节,王氏也大仇得报。
祝赵之变在明末为常熟一件大事,牵扯到邑中多家高门大户,事情以两败俱伤的方式结束,令人唏嘘。只是参与各方很快要面临一个更大的变故——甲申之变。明朝大厦将倾,清军铁骑即将征服大明王朝,各大家族也要重新洗牌。
尾声
祝家借此群体事件,着实出了一口恶气,但王氏清楚地知道,闹出这么大的事,得罪那么多缙绅大宦,祝家已经无法在常熟立足。王氏这位为夫复仇的奇女子,再度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自家宅子夷为平地,带着三个儿子远走他乡,下落不明。
组织缙绅会议、主持公道的瞿式耜在大明最后时刻尽显英雄本色。南京陷落后,南明经历弘光、隆武几个政权,最终覆亡。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在广西巡抚任上的瞿式耜拥立朱由榔于肇庆登基,这便是正史中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瞿式耜为不可为之事,尽必须尽之忠,以兵部尚书守桂林,终因寡不敌众,城破殉国。日后,桂林人建祠以纪念这位大明朝的末路英雄,瞿式耜也完成了自己的在三之节。
常熟钱家,自钱谦益祖父钱顺时、叔祖钱顺德科举登第开始显赫,到钱谦益时达到顶峰,钱谦益成为江南士林领袖。可惜在南明弘光政权覆亡之时,作为士大夫榜样的钱谦益嫌水太凉,未全忠节,而是开城门投降清军。其后,虽然他也曾为反清复明奔走出力,但终归与世俗的“成功”无缘。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钱谦益病故,享年八十二岁。钱谦益卒后三十四天,柳如是不堪被钱家族人索取家产,亦自缢身亡。
赵士锦随后为朝中官员推荐,在家宅拆毁尘土未定的十二月初八,复出为工部员外郎,赴北京任职,亲眼见证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的甲申之变。赵士锦写下《甲申纪事》《北归记》。北京城破之时,共有二十一名文官为大明殉亡,包括东林党名臣倪元璐。同为东林党的赵士锦既没战死也没自杀殉国,而是被李自成军抓住,曾被选用为大顺官员。后来他逃脱大顺军控制,跌跌撞撞回到常熟乡下,曾一度被任命为南明弘光政权的水司员外郎,南明覆亡后不知所终。
明亡后,赵士春也在乡间归隐不出,入清三十年后去世。赵家经历过鼎革大变,最终归顺了大清,重新参加政治活动,后来有赵士春孙子赵廷珪考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庚辰科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入清之后,赵家风评有所好转,后人也曾有过赈济灾荒、捐租田千亩的义行。清末,光绪帝师翁同龢在赵氏后人赵宗建墓志铭里,称赵同汇、赵元恺、赵奎昌“三世皆以义侠闻”。赵氏也得以被列入地方志“义行”中。看来,明末的国耻家难也让这个家族深深吸取教训,改换门风,方得以家门不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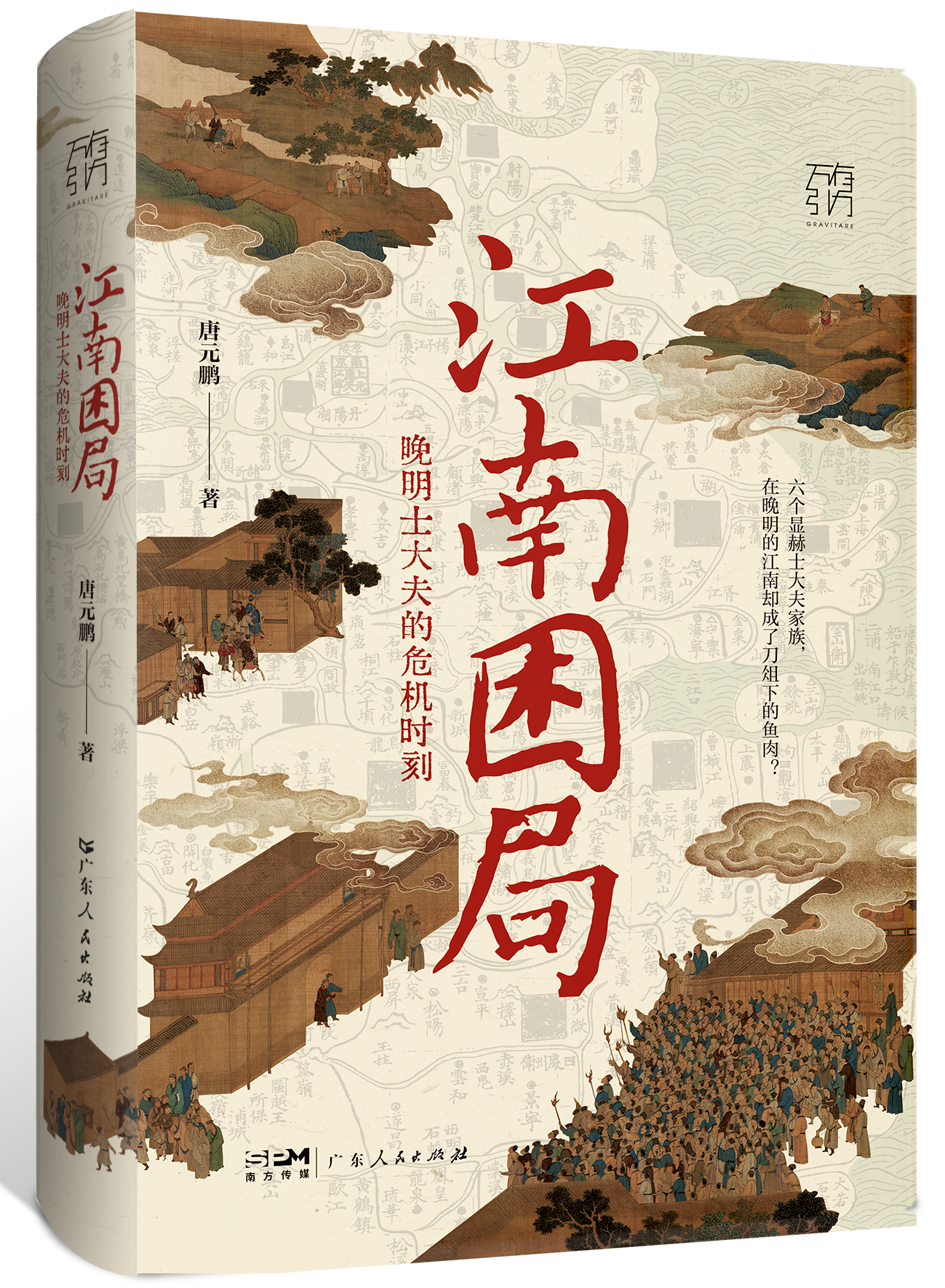
(本文摘自唐元鹏著《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