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关于流行艺术家的不当言论和行为,甚至某些犯罪行为的揭露比比皆是。加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公众对曾经喜爱的艺术家隐藏的生活开始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目光。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吗?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失德艺术家?以及,还能欣赏他们的作品吗?在《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一书中,作者运用哲学工具,为这一困扰我们的伦理问题提供了解答。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译林出版社授权发布。
那么,什么才算是团结声援受害者,而不是在哗众取宠地宣扬自己的道德纯洁呢?换句话说,成为有道德的艺术消费者,它最终意味着什么?为了获得答案,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具体的艺术案例中,考量哗众取宠所需的成本。我想表明的是,对失德艺术家的哗众取宠,不仅会让受害者成为工具,还会由于认为艺术仅仅关乎于道德,从而使艺术本身成了工具。要是说艺术世界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在艺术中,审美问题是无法退居二线的。可以肯定的是,正如我们在第一章里所讨论的,伦理和审美可以彼此密切相关。但是,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即涉及作品和艺术家的伦理问题会对审美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某种道德试金石用在我们消费的所有艺术身上,或者将艺术的价值降低到只剩下道德内容。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艺术就只是工具性的,它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仅在于它能够使我们成为道德上更好的人,或者传达无法言喻的道德真理。但是,想一想艺术(以及更广泛的审美事件)塑造生活的各种方式吧。你听音乐、看电影、往墙上挂画、决定衣着或者设计发型:这些都是与艺术和审美相关的决定,其中很多似乎与提升人的道德、采取道德或政治立场没有太大关系。再讲一遍,这并不是说它们不能有关系:就在这些艺术和审美的选择中,许多选择都可以具有重要的道德与政治意义。奇怪之处在于,有些人认为艺术就必须如此,除非是服务于某种道德上的重要目的,否则艺术就是没价值的。如此这般,我们的艺术和审美生活就臣服在了道德生活的脚下,而这与大众典型的审美行为并不相符。因此,对于强行要求必须这样做,不然我们自己就有不道德行为的观点,我们尤其应对它的后果保持关注。
在一些大众的艺术批评里,可以找到这种尤其具有误导性的例子,它们大力要求关注道德而忽视审美。每当带有争议道德内容的电影上映或书籍出版时,评论员(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但在更为权威的媒体上也是如此)甚至没有停下来研究作品的美学特征,就急着对道德上有问题的内容进行谴责。譬如,想想关于电影《小丑》(Joker)的争议,有些人谴责它美化了所谓虚无主义暴力——而大部分争论都是由那些甚至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提出来的。类似的道德义愤也曾出现在各类电影中,诸如《哈莉特》(Harriet),《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Richard Jewell)和《心灵奇旅》(Soul)。传达的信息通常很简单:不要看这部电影!但是,自称批评家的人,如果其目的在于警示艺术作品的不道德内容,那他不过就是个审查员而已,充其量是个评级代理。真正的评论,其目的在于理解。当然,评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部作品不值得观众花时间,但终究应该是鉴于它的审美价值而得出这种结论。可以肯定的是,道德特征可以影响审美特征,但认真对待这种关系,并不等同于说让道德因素完全盖过审美因素。仅仅用艺术批评来告诉人们哪些作品在道德上是坏的,就像仅仅用美食评论来告诉人们哪些食物是不健康的一样。我知道馅饼是不健康的!我想知道的是,那里的馅饼是否值得一试。
要清楚的是,这与受害者的痛苦是否被艺术家贡献的价值所抵消是不同的问题。举个例子,要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比尔·科斯比的表演和单口相声节目,就觉得他的连续性侵史是值得的,这样想就太可怕了(想象一下跟他的受害者这么说!)。这里的问题在于,在伤害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欣赏作品的道德代价是什么。我们可以借用奥斯卡·王尔德的故事来生动地说明这一区别。在王尔德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主人公的恶被保存为其肖像上的瑕疵,而这个男人自己却保持着青春和美丽。现在,假设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想象一下,原本格雷的肖像画是乏善可陈的,但他的不道德行径的直接后果,即令人毛骨悚然的版本,成了一件华丽的艺术作品。我们可以说,要是格雷没有做出这些改变肖像创作的行为的话,还是会更好一些,即使这意味着肖像的审美价值将会消失。但这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与我们在肖像出现之后应当如何处理它的问题不同。就算知道它在审美上的成功直接来自各种坏行为(敲诈、谋杀等),但我们为这幅肖像感到惊叹不已,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吗?有些人可能会抗议说,我们欣赏肖像,肯定就表示了对这些恶的认可,但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人是复杂的。我们可以一边不断谴责格雷的不道德行为,一边对格雷创作的艺术作品发出惊叹,即使那件作品本身还是让我们深感不安。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艺术是一个允许不确定性存在的领域。在艺术中,模糊不清可以是一种优点,包括道德上的模棱两可。大家对这一点很熟悉,就连大学预修英语文学考试的论文提示都建议考生为道德上具有模糊性的文学人物撰写文章——大学理事会并不会因其有争议的观点而惹来争议。但这恰好就是我们在讨论艺术家的道德不端行为时,事情变得棘手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小说世界中,对道德的模糊不清进行探讨,但在现实中没有这份安全感。当谈到艺术家的实际行为时,就存在着真正危在旦夕的生命和真正的受害者。我不想夸大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区隔:艺术当然可以对世上发生的事情造成影响,无论是好是坏。但是,人们对艺术作品所采取的态度是否适当,部分地取决于艺术的功能;现实世界并没有像艺术世界那样,为作品的解读提供一个保护区域。
虽然我认为,一件艺术作品的道德缺陷确实能与审美关联起来,但我并不太想要为这些缺陷而担忧。欣赏汉尼拔·莱克特这位堕落的天才,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如果有,那我也不想成为正常人了。小说和电影是虚构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探索人类阴暗面的空间。尽管这部电影的伦理非常复杂,但我对宣布自己喜爱《沉默的羔羊》毫不内疚;相反,它对我的吸引点之一,正是其复杂的伦理。我在课堂上曾多次透过这部电影讨论艺术的伦理批评,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为影片对残暴丑恶、女权主义和跨性别恐惧症的处理做出精彩的观察,并且往往又彼此不同意。在一篇很棒的论文里,莱拉·D.蒙特埃罗(Lyra D. Monteiro)捕捉到了这一现象。她描述了她在大学初期第一次读到一本书的经历,这本书成了她批判性解读《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的工具,那是她童年时最喜欢的电影。她写道:“这种深入的批评丝毫没有动摇我对这部电影的喜爱;相反,它让我更加热爱这部电影。我的确真是这么做的。我完全可以想象,这部1960年代由英国白人创作的电影在种族、性别和性方面存在问题。而我喜爱这部电影也没有问题,喜爱它是因为它的缺陷,而不是尽管它有缺陷。”
蒙特埃罗的评论可以与我前文描述的说教式“批评家”形成对比。这感觉就像是,那些希望我们停止观看和阅读具有复杂道德内容的电影和书籍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太关心艺术;而道德的复杂性正是使艺术如此难以抗拒的部分原因。它具有挑战性,令人寝食难安,它邀请我们反复品读,生出不同的视角。关键并不在于我们必须热爱任何及所有具有道德挑战性的艺术。我认识、钦佩并尊重的一些人,他们喜欢那些远超我承受程度的堕落电影,这没关系。我无法让自己去看《趣味游戏》(Funny Games)或其他有时被归类为“性虐待”的电影:坦率地说,我害怕这些电影。但我不认为,欣赏这些电影的人就是精神病。我的意思是,当然了,这是有可能的。不加批判地消费艺术,这总是有可能的,这些消费者只不过是透过艺术来关注自己的乖张态度。这就是电视评论家艾米丽·努斯鲍姆所说的“坏粉丝”。但在这些情况里,问题显然出在人身上,而不是艺术作品。可以肯定的是,很多艺术都是糟糕的,而在道德上带有恐怖内容的坏艺术会更加糟糕。关键在于,作品中有道德问题的内容,可能是使其引人入胜和值得欣赏的部分原因,但这只是可能而并非必须。
我们于是便学到了,重要的是那些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内容在作品中的作用,而这也可以为我们在欣赏失德艺术家的作品时提供指导。正如上一章所讨论的,有时艺术家的行为会影响到对其作品的解读,有时这二者又会毫不相干。想一想《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 K.罗琳的例子。罗琳最近因为在性与性别方面有误导性的偏执推文而招致了粉丝的愤怒,这些推文歧视了跨性别者和非性别常规者。我们投入罗琳所创造的虚拟世界,但她的态度会对我们的欣赏造成怎样的影响?对于那些跟着《哈利·波特》一起长大,并热爱这个魔法世界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尤为紧迫的问题。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回到审美之爱的问题;在此,我仅想用这个例子来反思一个有点不一样的问题。因为,尽管事实上我读过每一部《哈利·波特》的书,也看过每一部《哈利·波特》的电影,但我真的不爱《哈利·波特》。我甚至不是特别喜欢它(如果我们谈论的是魔法学校的话,那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地海人)。然而,我也是一名家长。最近我和孩子一起读了《哈利·波特》第一部,然后看了它的一场电影。作品真是热门!我还收到了一件可爱的T恤作为生日礼物,上面的图案是海德薇叼着霍格沃茨的录取通知书。在罗琳的推文之后,我对这一切就感到了不舒服。我们消费艺术的大多数决定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但对于家里有小孩的人来说,我们也会代表孩子做出消费决定,塑造他们所接触的事物,以及他们可能会爱上的事物。我应该因为作者的一些推文而限制我孩子对《哈利·波特》的消费吗?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即在原著改编电影中扮演哈利·波特的演员,发表了一份声明回应罗琳的推文。以下是声明的核心部分:
我真的希望你们不要因此而完全丢弃这些故事中对你有价值的部分。如果这些书告诉你,爱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如果他们告诉你,力量存在于多样性中,而教唆纯洁的教条观念会带来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如果你认为某个特定人物是跨性别者、非二元性者或性别流动者,或者他们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如果你在这些故事中找到了与你产生共鸣并在你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帮助过你的东西——那就是你和你读的书之间的事,它是神圣的。在我看来,没有人能触及它。它对你的意义,就是它对你的意义,我希望[罗琳的]这些评论不会对它造成太多玷污。
雷德克里夫的陈述,让我们想起上一章讨论作者的意图谬误与死亡时所介绍的一些想法。艺术批评界一直在争论,我们在解读作品时应在多大程度上遵从作者的生平或意图。雷德克里夫的评论,却提出了一个有点儿不一样的问题。重要的并不见得是作品本身的意义,而是作品对你的意义。无论我们是否认为一件艺术作品具有特定的意义,或者觉得这种或那种解读方式更加准确,这些都可以跟作品对个人的意义区分开来。一部作品对个人的意义,取决于它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而在这一点上,我们才是作者。现在,作品对个人的意义,可能会与揭露原作者而出现的新认知发生冲突,这可能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情感体验,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回到这一点。目前,我的观点仅在于认为,我们可以合理询问作品的意义,询问欣赏作品的表达意义,但这些问题并不总会影响到作品对我们的意义。它可以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领域,或者是一个我们为年轻人提供积极保护的领域。或许在某个时候,我想和我的孩子谈谈J. K.罗琳以及她对跨性别者和非二元性别者的看法,但肯定不是在我们扮成赫敏·格兰杰的时候。
上述观点讨论的不仅是已为人们所喜爱的作品,对于那些人们还未曾品读的作品来说,这个观点也同样适用。换个例子,我不认为罗尔德·达尔是公开反犹太主义者这一事实,意味着人们不应该给孩子读他的书(或者自己不阅读他的成人短篇小说)。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一些书里,也包含着各种有问题的表述(我说的就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但学习批判性的阅读,就需要复杂的文学作品。我想象自己决定不给我的孩子读《了不起的狐狸爸爸》(Fantastic Mr. Fox),然后被问到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我要说什么好呢?说我不想给达尔提供经济支持?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我却拥有这本书。说我不想成为他反犹太主义的同谋?要是觉得给你的孩子读《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就会让你成为反犹太主义的同谋,那可真是对同谋这个概念的嘲弄。罗尔德·达尔的粉丝群体,并不是什么反犹太主义或造成伤害的群体。如果我们想让同谋这个概念在道德上发挥重要作用,那它就不能是只讨论这些鸡毛蒜皮的单薄概念。
有时,当我们无法为某个决定提供令人信服的支撑理由时,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触及了道德的基石。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先将该决定视为已给定的,然后从实际中做出归纳,并对其更广泛的意义加以考量,从而对这个选择进行评估。借用去年一篇病毒式文章的标题来举个例子,“我不知如何向你解释你应该关心别人”。当然,我可以通过哲学的方法,尝试从更为基础的道德承诺中推导出这个真理,但我觉得,这就是最为基本的东西。一个人们互相关心的世界,看着就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种道德承诺,与其他类似的基础性的道德原则是相互一致的。
相比之下,要是有这么一个世界,只要艺术家有不良的道德信念,我们就自动停止接触他的艺术作品?我可不想生活在那个世界里!一个因为达尔晚年在采访中说了一些可恶的话,我们就拒绝《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的世界吗?不要,谢谢。我更喜欢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明确表示达尔的观点是令人憎恶的,但我们不会通过将他捧上神坛而掩盖真实,我们还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有不良道德观点的人仍然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与另一条基本原则(我们应该关心他人)的情况不同,如果生活在一个将抵制失德艺术家视为道德基石的世界里,那我们要失去的东西可就太多了。我们将失去不计其数的艺术,并不是因为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怪物,而是因为人类在道德上就是复杂的。正如泰勒·马龙所说:“每个艺术家都有着道德、社会和政治上的缺陷。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都是丑陋、杂乱的人,但这也是因为道德、社会和政治上的缺陷会呈现变化,取决于做出判断的人、地点、时间以及文化。”马龙论述的第二部分,暗示了(我并不赞同的)某种程度的道德相对主义:譬如,我认为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当时在道德上是极为可怕的,即便它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而这不是说,仅仅依照今天的标准来说它是道德错误的。然而,出于不同的原因,他的观点在此仍然是适用的。即使我们假设道德是客观的,但不同的人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文化,他们就难免会在道德判断上出错,而导致决定哪些艺术家会因他们的信仰或行为而遭到唾弃的,正是这些人对道德的看法(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不仅会失去很多艺术,而且会因为莫须有的理由而失去很多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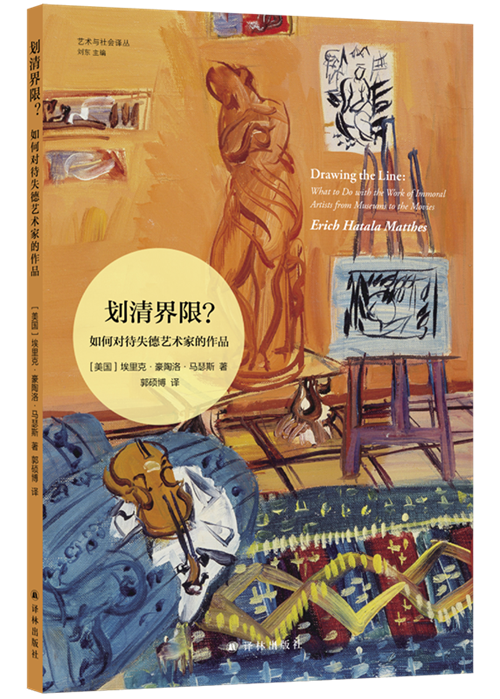
《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美国]埃里克·豪陶洛·马瑟斯著,郭硕博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8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